摘要:本文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香洲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民初廣東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的考察,充分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後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博彩業與粵港兩地博彩業早期關係為“此興彼衰”,而到了民國初期,澳門博彩業則為較少受到或不受粵港兩地賭博政策的影響,這種關係轉變的深刻原因更是值得考究。
關鍵字:澳門博彩;辛亥革命;香洲開埠;立憲運動;廣東博彩
結論:本文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香洲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民初廣東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的考察,充分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後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博彩業與粵港兩地博彩業早期關係為“此興彼衰”,澳門博彩業較大程度上受到粵港兩地政府弛禁賭博政策的影響,甚至兩地的賭博政策關乎澳門博彩業的生死命運。而到了民國初期,由於大部分賭商實行狡兔三窟的策略,分別在澳門和廣東開設店號,廣東省的風聲不對,就轉往澳門繼續經營,極大地降低了開賭館的風險,此時的澳門博彩業則為較少受到或不受粵港兩地賭博政策的影響——廣東的禁賭和開賭,對澳門的博彩業已不再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澳門政府只等坐收漁利便是了!
後記:此文係提交給2011年9月份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的“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屆學術年會”的會議論文,第一作者為胡根先生。論文的架構、思想等均來源於胡先生,而我只是做了一些後期文字的技術處理工作,其實是不夠資格成為為作者的。2012年5月我離開澳門後,對於該論文集的出版詳情並知曉楚。2014年4月,再次訪問澳門時發現了這本書,更令我驚喜的是我的名字竟然忝列其中,這不得不感謝胡先生的大度與提攜。 胡根先生曾師從湯開建教授,專著《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的出版奠定了其澳門博彩業研究的重要地位。胡先生雖身為澳門特首行政長官辦公室顧問,但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一直熱心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實屬難能可貴。在其積極推動下,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的年會如今已經連續舉行了十二年,每年均出版有《澳門歷史研究》專輯。2014年第十三屆澳門歷史文研究會也將於9月舉行,擬定的主題為“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希望諸位有興趣的專家學者積極參與。
出版信息:胡根、馬光:《辛亥革命前夕的澳門博彩業》,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版,ISBN: 978-99965-2-048-8,第480-491頁。
在線閱讀顯示效果欠佳,建議下載PDF文檔后閱讀。
辛亥革命前後的澳門博彩業
澳門的博彩業由來已久,據考早在1810年,爲了給葡萄牙人開辦的慈善組織——仁慈堂籌募善款,澳門政府於該年就已經批准發行西式彩票了。[1]1846年2月,當時的澳門總督比亞度就發出了准許開設番攤賭館的總督訓令,後來其繼任者亞馬留總督把中式賭博,如番攤、闈姓、白鴿票等加以合法化。[2]從此,澳門的近代博彩業從此得以迅速發展,最終成為了近代澳門政府稅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澳門博彩業史是近期“澳門學”研究中的一個頗為熱點的論題。近幾年有幾位專家學者相繼投入了這一課題的研究,將澳門博彩業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更深的層次。然而,對於澳門辛亥革命前後澳門博彩業的整體發展情況,學界尚付之闕如。本文擬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香洲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民初廣東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的考察,來展現辛亥革命前後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
澳門與粵港:博彩業此興彼衰
粵港澳地區緊密相連,早期的澳門博彩業受到粵港兩地的影響頗大:兩地若禁賭,則澳門的博彩業就興旺發展;兩地若弛禁,則澳門的博彩業就會陷入窘境。概而言之,澳門博彩業與其他周邊地區,尤其是與廣東的關係可謂“此興彼衰”。
劉坤一、張樹聲治粵時期(1877-1884年),粵省實行禁賭政策,而澳葡政府卻看准時機將賭博全面合法化,公開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等粵人喜好的賭博,同時允許在市區和離島售賣鴉片煙,形成“黃賭毒一條龍”。此舉一出,內地賭徒紛紛到澳門搏殺,形成了澳門賭業的有一個高峰期。1880年8月1日的《申報》曰:
彼澳門西官以為人棄我取,粵省香港既已禁止凈絕,則賭徒之生業頓無所賴,然平素恃為生涯,而一旦棄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門舊有賭館,有不絡繹趨赴者乎?合省港於澳門,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盛乎?此所以每年繳賭稅有百數十萬之多也。[3]
《申報》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澳門的賭博“以三合一”,怎麼會不更加興盛呢?澳門博彩業的興盛也可以從不斷提高的承充費中得窺一斑:
光緒四年以期滿加價,復充三年,繳葡萄牙軍餉六十萬金,名曰時和闈姓公司。光緒七年又以期滿加價,復充三年,繳葡萄牙軍餉九十萬金,名曰怡安闈姓公司。是省城商民及四鄉州縣往澳門投買闈姓者,仍不能禁止,而愈開愈熾。[4]
中法戰爭爆發後,廣東為加強軍備,所需錢款甚多,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在此形勢下,下令招商承充闈姓,以資軍需。此政策一出,即吸引了許多賭商從澳門北上逐利,回到內地重新開業。
廣東闈姓的賭博再次復蘇,此舉對澳門的闈姓賭博打擊甚大。最明顯的例子是祥興公司東主黃成興於1884年5月投得澳門、氹仔和路環闈姓之後,因廣東弛禁而大失預算,被迫放棄已經到手的承充權。1885年3月《申報》有這樣的報導:“聞澳門闈姓館於去臘尾緊閉門戶,席捲一空,凡業經投標者無由追問矣。”[5]同時,澳門政府的闈姓收入也驟降,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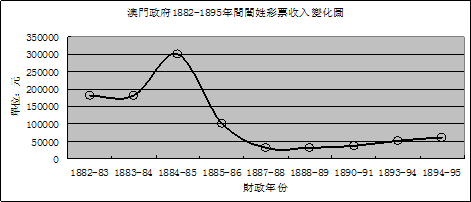
據圖分析可知,澳門政府的闈姓彩票收入在1882-83年和1883-84年都超過了18萬元,1884-85年更是高達30.06萬元,但是到了1885-86年卻驟然下降到了10萬元,還不到1884-85年的三分之一,而1887-89年間的收入更是跌倒谷底,祗有3.06萬元,祗是廣東未開闈姓前的十分之一而已,跌幅甚大。[6]
闈姓生意在這段期間雖然受到掣肘,但是以番攤為主的雜賭卻依然旺盛。1887年途徑澳門的葡萄牙貴族阿爾諾索伯爵在其回憶錄中提到:
在華人區裏有許許多多的從事番攤的賭館,賭館裏點著燈籠和蠟燭,白天全天對外開封,晚上一直營業至午夜。[7]
這時期的番攤博彩稅收,也能保持穩中有升,從110500元增加到119260元。[8]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闈姓賭博收入驟降而其他賭博收入卻穩中有升的怪現象,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受到了廣東省闈姓賭博弛禁而其它賭博並未開放的影響。
不久,隨著李瀚章的被查辦和開缺回鄉,粵澳兩地的賭業形式又發生了逆轉。1895年正月馬丕瑤就任廣東總督後,開始實行禁賭政策,並在同年10月在澳門的報紙上宣佈廣東當局嚴禁賭博以肅清盜源。[9]此項措施對澳門的博彩業無異於久旱逢甘露:
自省城禁絕番攤之後,澳之攤館十六家,異常熱鬧,每至燈時,幾無坐立之處。蓋城鄉來澳之眾,多有賭癖也。連日闈姓各廠,更為熱鬧。初十、十一兩日,京電紛馳投猜恐後,門限幾為之穿,延至夜分,猶然逼塞一堂,非負雄力者不能求立足地。[10]
從以上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廣東的賭博政策瞬息萬變,而澳門的政策則十分明朗、穩定,澳門也就逐漸成為了中國最大的賭埠了。及至1897年,闈姓賭博已悉數集中在了澳門,“唯刻下省垣已無闈姓廠。嗜賭之輩,均向澳門購買”。[11]
香洲“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
清末的香洲“開埠”,在粵澳關係史上是一樁重要的事件。究其原因,既與中葡就澳門劃界事務的爭議有關,亦涉及禁賭問題。
香洲是清代廣東對外開放的九個商埠之一(其餘八個為廣州﹑潮州﹑瓊洲﹑北海﹑拱北﹑三水﹑江門﹑臺山公益)。與香洲同時“開埠”的還有臺山公益,均為兩廣總督張人駿批准開辦。[12]其實,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間,盛宣懷等就曾打算在澳門對面島開設商埠,但此議受到廣東地方官員和百姓的反對,未獲朝廷允准。外務部在回電呂海寰﹑盛宣懷時說:“澳門對面島請開商埠,粵省督撫及香山縣百姓均不樂從,此條斷不可允。”[13]
香洲舊屬香山縣(現屬珠海市),光緒三十三(1907)年,清政府實施“新政”,鼓勵華僑實業家回國投資。次年(1908),邑人王詵和美國僑商伍于政計劃集股在香洲開埠,於1909年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出現一場威脅澳門博彩業乃至整個澳門生存的“香洲開埠”危機。
“香洲開埠”立約時,曾表示要永遠禁賭,但香洲開埠需要集股,很多商人其實是想在香洲另起爐竈,與澳門博彩業爭一日之長短。但是,廣東禁賭之聲日益高漲,清廷又沒有弛禁賭業的跡象。據《香山旬報》載,香洲開埠工程開展不久後,就有商人向兩廣總督袁樹勳提出申請,希望“弛賭禁”。此說立即引起民間禁賭人士、團體和輿論的反對。有輿論認爲,這樣做只會使新成立的香洲商埠變爲第二個澳門。[14]
廣東勘界維持會在省城廣州舉行的會議上,有商人以遏制澳門爲名主張香洲開賭,但馬上招來一片反對的聲音。《香山旬報》第八十期刊登了一段署名為“民聲”的時評,力斥其“不智”,不但不能夠影響澳門的賭業,反會損害香洲新埠。文章指責說:
以爲香洲開賭,足以奪澳門之利,而張香洲之勢,此真童雅之言也。夫當禁賭時代,而倡開賭之說,已非人情,然香洲開賭,確足以制澳門之命,猶可說也,乃按之事實,適得其反,諸公試思之,我國處處有賭,時時有賭,何嘗損澳門分毫之利益,又何論香洲一隅之地乎?香洲以新闢之地,商務未盛,而竟導人以賭,香洲商務之蒙損害者,爲至多且巨也。[15]
在這一時期,香山縣境內賭風日熾,對社會風氣及治安影響甚烈,報章時評:“大黃圃賭風甲於別鄉,雖經地方紳士屢次升紅請示禁止,然皆視若等閑,警界內所設諸般賭博皆備,如北帝廟等處尤衆,近更各藥材店,亦多有喝雉呼盧。”該斷時評挖苦主張香洲開賭的人:“某君倡議,由香洲埠設賭以抵拒澳門,毋乃該鄉人亦作是思想耶。”[16]
香洲開埠對澳門當然會有巨大的影響,由於受到中方的壓力,以及廣東尤其是香山縣民衆的抵制,澳門商務大受打擊。澳葡政府在這段時期入不敷支,財政困難,仁慈堂彩票無人肯投充承餉。香洲醖釀開埠之初,澳門的華商就曾經與葡商共同商議對策。會議建議葡國方面採取五項措施以挽危局:一、速飭勘界大臣來澳;二、授全權與澳督,一切章程便宜施行,不爲遙制;三、廣澳鐵路事速行;四、將1904年在上海所立之約從速批准互換;五、准澳門立即興工浚築內河。[17]葡人社會對香洲開埠一事也非常緊張,認爲此舉會對澳門社會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18]澳葡當局惟恐當地商民離澳遷往香洲,在勘界問題上被迫退讓。[19]中國民眾憤怒的聲音,也迫使清廷不得不對葡萄牙人的擴張要求予以拒絕,葡國的勘界大臣馬楂度在1909年10月30日的日記中提到:
(高而謙)顯然為會社的恐嚇和對煽動暴亂行為的擔憂所困擾。否則的話,我相信他可能會讓步。他認為我更有影響和駕馭局勢的才能,所以請我想一個中國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在他看來,此事對我們來講其利益和重要性根本無法和對中國的相比,在那裏它可能會招致嚴重的事件。[20]
屋漏又逢連夜雨,因受內地官民的抵制,由內地前往澳門的旅客人數劇降,番攤賭館、人力車、豬肉攤販等行業慘淡經營,與澳葡政府為稅務問題發生矛盾,導致人力車伕罷工,肉行要求減稅。[21]1910年3月22日的《華字日報》稱:“澳門倒閉之商店:聞澳門生意極淡,寶生銀號、順合當押及致新洋貨店,皆已先後倒閉。”[22]
宣統三年(1911)年初,粵督張鳴岐親到廣東自治研究社,與諸紳商討論禁賭問題,先由張鳴岐對衆人“陳說禁賭之必要,及勉勵紳商各宜擔負責任,以補官力所不及,並申明定期三月初一日概行將賭禁絕,決不展期。”會上有人提出:“若粵省禁賭,而澳門不禁,決無效果,應請制憲照會澳督,一律施禁,利權不至外溢。”[23]張鳴岐隨即問各紳商有何禁賭善後條陳?眾紳商建議“禁賭之後,倘有私開,初犯各罰款一百元,再犯加倍,連犯三次,則酌予監禁。”張鳴岐覺得言之有理,乃令各紳商議定罰款章程,交廣東省諮議局臨時會審議。[24]
在粵省厲行禁賭後,張鳴岐派人調查澳門賭業,發現澳門的大小賭場“日益暢旺。”隨即張鳴岐設法與澳葡當局展開交涉,希望澳門能夠配合廣東的禁賭政策。[25]據《香山旬報》載:
澳門禁賭一事,前經與澳督磋商,尚未實行,現張督以粵省禁賭後,而澳門不同時禁絕,雖經交涉,亦恐難就我範圍,惟澳門賭博,皆屬我中國子民,自應遵守中國法律,亦應一並嚴治,現先行嚴飭前山交界地方官嚴察查緝外,仍一面與澳督磋商,務將澳門賭博禁絕。[26]
清廷向駐法兼使葡國大臣劉式訓、駐英大臣劉玉麟電稱:粵督曾商請英政府轉達葡政府禁止澳門賭博一事,英使稱,應由中方自行向葡萄牙政府交涉,英政府可從旁贊助。[27]實際上,澳葡政府卻採取拖字訣,沒有真正在澳門開展禁賭。張鳴岐無奈,惟有下令:
嚴守疆界,堵截賭商攜帶彩票往來粵澳兩地。中國人民自應遵守中國法律,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如有違犯,罪其父兄,或削其身之應得權利,再由香山令前山同知查緝,以期有犯必懲云。[28]
之後,張鳴岐便派人在澳門前山交界等地方嚴密查緝澳門賭票,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陸路有兵勇把守,賭商就走水路帶票。據報載:“澳門賭商近與省澳輪船公司訂明,凡赴澳門賭博者,減收船費,由各賭館抽回費用,以爲津貼,並設一種特別減價券,俾賭徒作爲船票。”[29]利之所在,賭民賭商如蟻附羶,廣東當局欲禁無從。
清廷不但未能對澳門的賭業採取任何限制,還反而被葡萄牙人插手廣東的禁賭事務。1911年3月《申報》刊登了一段新聞:
粵督昨據靈山高令稟稱,卑縣自到任後,對於私自開攤館一事,均極認真嚴禁,常微服親查,以故私開者不敢明目張膽。前月初十日,據三合墟巡警稟稱,該墟周煥章家內有私開女攤等情。卑縣據此,當即派差會同該巡警前往,當場拿獲共男女等人十二名,押解到縣,並將周煥章房屋查封。現由葡國遊歷洋人荷那威林出爲幹預,致函縣署,謂此屋系伊友産業,請即揭封交還等語。業已復函拒絕,應請照會該國領事,飭知該葡人立速離境,勿庸幹預。[30]
此時,香洲新埠卻因大火和王伍等人的舞弊案件陷入困局。香洲新埠開張之初,曾經搭蓋葵廠百餘間,次年六月突然被一把火燒個精光,“所存者僅瓦鋪四十餘間。日來因有在該處鬥蟀演戲開設賭場之事,現爲恭都局紳鮑桂芬等,據情向督院呈控云。”[31]火燒香洲新埠的原因不明,可能是失火,也有可能是有人縱火。但無論如何,這場大火對埠商的打擊極大。香洲開埠流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埠商王詵、伍于政等並未真正投入資金,而是以開埠爲名轉售土地漁利。二人起初主張禁賭,開埠後卻又出爾反爾,要求弛禁,以致失去地方紳商和民衆的支持。[32]及至後來,投資者見清政府對香洲無稅口岸遲遲沒有批准,[33]以及埠務出現內訌,非常失望,紛紛轉移資金,商店也隨之倒閉,整個香洲變成一個廢墟。
在“香洲開埠”事件中,雖然朝政腐敗,國力仍然衰微,但中國人民對外侮已忍無可忍。在國內外同胞憤怒的吼聲中,清朝中央和廣東地方政府聯合民間愛國力量採取一致對外的行動,從經濟和軍事上對澳葡當局的擴張行徑作出一定程度的反擊,只不過朝廷的態度後來軟化了。而從效果來看,“香洲開埠”本身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中國卻在外交、軍事上成功地向澳葡政府施加了壓力,遏制了葡萄牙當局再次擴張的意圖。
澳門的博彩業在“香洲開埠”事件中確實一度受到嚴重的威脅,如果當時香洲真的成功開埠,澳門賭業的發展必定會受到掣肘。但是,“香洲開埠”由於諸多內外條件的限制,而未能成功,所以並沒有真正動搖澳門賭業的基礎。然而,廣東人民在這次事件中更加看清了賭博對社會的危害,禁賭的意見再度佔據了上風。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以及民國的成立,內地禁賭的聲浪日益高漲,澳門的賭業乃得以獲得一段相對穩定發展的時期。
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
清末廣東賭風禁而不絕,朝廷廢科舉之後又試特科,廣東的闈姓死灰復燃,直到宣統元年(1909)八月,時任廣東巡撫兼署理兩廣總督的袁樹勛向朝廷奏報:
查粵省賭博之為害,萌孽於三十年以前而騰躍於近十年以內。本年五月間,前督臣張人駿曾遵旨覆陳,賭餉出入大宗,以為實行禁賭必先妥議抵餉,嗣後粵省無論籌得何款,均先儘賭餉撥抵。務期賭博陸續禁絕,賭餉次第停收。並俟諮議局成立會集議員妥商辦理。[34]
袁樹勛提出,應杜絕澳門彩票流入廣東,只要中國自強,自能據理阻止。他表示,今後將不准在粵賭館發售宣統二年(1910)之彩票。[35]袁樹勛所指乃是禁止闈姓彩票一項,但不包括番攤及基舖山票等其他彩票。斯時廣東賭風大盛而盜賊四起,令地方官員和朝廷極為頭痛。一時間,禁賭和籌餉竟成魚與熊掌,難以取捨。力主禁賭的袁樹勛認為“賭博有百害而無一利,一鄉一邑設一學校不敵設一賭館,習染移人子弟,多暴教育將何所施”,進而建議“一邑籌抵有款則禁一邑,一鄉籌抵有款則禁一鄉。向無賭博之處應立案永遠不准設賭。”[36]
1909年10月14日,廣東諮議局成立。斯時闈姓賭博已壽終正寢,但其他賭博仍然盛行未衰。賭博對社會和民間的危害,已達怨聲載道的地步,民間一片禁賭的呼聲。官府下令鋪票、白鴿票以及其他雜賭一律禁絕,然而晚清吏治腐敗,收慣賭館陋規的大小官員怎肯就此罷休?利之所在,實難以杜絕。如《清稗類鈔》載:
宣統庚戍,粵人以番攤害钜,公請永遠禁止。時督粵者為張堅白制軍鳴歧,甚韙其議,遂於辛亥春奏準停止賭捐,即日實行,省內外番攤館千餘家,一律禁閉。然私開攤館,潛納陋規者,猶未絕也。” [37]
“香洲開埠”事件之後,賭博對廣東社會危害之烈更為民衆所側目。宣統二年(1910)三月,廣東籍京官胡蓉弟等向朝廷奏報:
廣東賭害甚烈,胥一省之人,無貧無富,無老無少,群陷溺於賭博之中。蕩產傾家,強壯者散為賊盜,老弱者流為餓莩。甚至婢僕因賭起竊,為家長呵責而輕生﹔婦女因賭喪財,為匪類引誘而失節。種種禍端,不堪枚舉。是以廣東盜風甲於他省,賭害一日不除,即盜風一日不息。或謂廣東賭餉,皆為待支的款,一旦短收,勢必支絀異常,諸事更形竭蹶。職等亦知賭餉甚钜,籌措為難。然粵省以富庶著稱,出入款項,果能認真整頓,亦無難籌措。”[38]
粵省民衆對賭博之憎恨,很快又遷怒於時任兩廣總督的袁樹勛。1910年8月13日,御史胡思敬上摺參奏袁樹勛前後重要贜罪凡五款,其中一條就是“初在廣東,揚言禁賭,得賭商賄三十萬,因以全省鹽務交賭商包辦,事成許再酬二百萬。皆一一有據,應按律懲辦。”朝廷聞訊即諭令“確切查明,據實覆奏,毋稍徇隱。”[39]宣統二年八月下旬,署兩廣總督袁樹勛向朝廷奏報:
遵查粵省鹽務規費,此次鹽務改良,其前提既純為移抵賭餉……並陳增餉抵賭,為數不敷,試辦膏捐數月,收數尚旺。擬自實行禁賭之日起,每年截留二百萬,餘候部撥。惟膏捐亦非經久之款,停止以後,鹽餉又歲有遞加,似可藉資賡續。其餘尚短賭餉七十餘萬,則煙酒兩項,當可酌量籌捐。”[40]
斯時正值清末立憲運動風起雲湧之際,諮議局的出現,迫使地方督撫不得不正視民間禁賭的呼聲。10月22日,廣東諮議局向朝廷呈請“明定廣東賭博一律禁絕期限,一再陳議,情詞迫切,請旨辦理。”[41]
賭餉收入可觀,但民間的輿論壓力也不容忽視。在權衡禁賭的得失之後,朝廷覺得廣東全面禁賭的時機已經成熟。1910年12月4日,朝廷降諭:
廣東禁賭,部議以籌抵賭餉未足為辭。查資政院預算,廣東歲出入總數,計宣統三年所入,實溢三百餘萬。……核計該省賭餉不過四百餘萬,除鹽務加餉,可實抵二百萬外,據督臣袁樹勛奏,煙酒等捐,亦可得二百萬以外。以所溢者撥抵,尚綽有餘裕。粵民籲懇甚切,請飭兩廣督臣即日禁絕。[42]
但是,已經取得各種博彩承充權的賭商們又怎肯善罷甘休?加上禁賭的前提是必須從其他管道得到“抵餉”之款,廣東省咨議局內也有不少反對禁賭的議員,因此禁賭政策也並非那麽容易推行的。因關係重大,朝廷也不敢催得太緊。到了該年12月30日,朝廷諭令:“廣東限期禁賭一案議決情形一摺。著度支部﹑兩廣總督,按照所陳各節,體察情形,妥定期限,奏明辦理。”[43]
次年(1911)1月2日,學部右侍郎李家駒等奏:“粵省賭餉抵款有著,懇恩降旨迅禁,以革秕政而除民害。”[44]
不過,廣東省的賭商聞風又拖欠應繳的賭餉,使地方政府進退兩難。爲此,朝廷只得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查辦承賭的商人和經辦官員。[45]
經過多年的弛禁歷練,廣東的賭商對付官府已是相當有經驗。明賭易禁,私賭卻難以取締。聞奏後,朝廷於1911年8月8日嚴令兩廣總督張鳴岐﹕“粵省私賭盛行,請飭實力查禁一摺。著張鳴岐按照所陳各節,嚴飭所屬,認真查禁,務絕根株。”[46]
張鳴岐本想從宣統二年(1910)8月1日起開徵酒捐,另闢財源,以抵撥賭餉,但又受到酒商的反對,只好暫緩開徵。[47]次年正月,官方舊話重提,酒米行商竟以罷市要脅。[48]另一方面,由於受禁煙運動影響,廣東省原擬由熟煙膏牌照捐所得年餉二百萬両亦難以成事。[49]不得已,朝廷把一部份洋藥進口加徵稅收劃撥給廣東,以抵補禁賭所引起之財政損失。可是,扣除了用於應付其他各項緊急要需的部份之外,餘下可充抵撥賭餉的款項大於只有1528000両。到了年中,廣東省從各方面只籌得2570118両,相抵之下,財政赤字約為二百萬両。[50]
1911年8月16日,張鳴岐向朝廷奏報的數字更爲具體:“粵省原收賭餉四百七十六萬五千七百餘両,今因禁賭,籌款抵補,本年尚不敷銀一百九十六萬八百両,擬籌藉以濟要需。”[51]無奈之下張鳴岐只得用舉借外債的辦法來解決。[52]
財政方面的問題勉強解決之後,在貪官汙吏的包庇縱容之下,民間私賭又屢禁不止。爲了掃除禁賭的障礙,1911年8月20日,兩廣總督張鳴岐向朝廷奏劾一批文武官員,其中有:“市橋汛外委傅榮高,候補千總,前署鐘村汛把總陸汝恭,裁缺井汛把總,前署東圃汛外委羅德華,均私收賭規,俱著即行革職。”[53]
在付出高昂的代價之後,廣東省終於實現全面禁賭。
民初廣東禁賭有名無實
然而,在廣東省厲行禁賭的同時,澳葡政府卻加緊招商承賭,趁機大發橫財。這樣一來,不但無法遏止熾熱的賭風,而且把開賭承餉之利拱手送給洋人,當年廣東禁賭“利歸他族”的歷史將會重演。
6月29日,張鳴岐向朝廷電奏時提及此事:
查粵自三月朔日禁賭後,省會賭徒紛紛咸往澳門誘人聚賭,且聞葡官有招人勸餉承賭之事,實爲粵民切骨之害。賭風一日不盡,盜風一日難除,其理有斷然者。此事已商數月,本擬即請鈞部與葡交涉,因粵省賭餉甫經停止,誠恐內地各屬間有私賭尚未淨盡,轉爲葡人藉口,是以先飭各屬切實嚴查,務令一律禁絶,再擬電商辦理。……粵中賭博之害甲於各省,而澳門一地尤爲各賭所集之區。本年二月間港督來省,因聞粵有禁賭之事,極力贊成,且稱賭博爲社會製造各項不法媒介,香港及新租界等處彼已飭屬嚴禁,以期掃此陋習。等語。歧當面謝其意,並以澳門賭風最盛,中國政府如向葡人商請禁賭,擬請其贊助,港督亦即慨允,屆時當請英政府贊助。岐因與商明,俟粵呈請政府與葡交涉時,再由港督請英政府同時提議。[54]
他又希望朝廷透過外交途徑向葡人施壓,務令粵港澳一體禁賭:“現在港督既已達彼政府由英使面允贊助,此機斷不可失,應請鈞部電知劉使向葡交涉,並請英使電彼政府設法贊助。”[55]
一個星期之後,即宣統三年六月十一日(1911年7月6日),朝廷在發給駐法國大臣劉式訓、駐英國大臣劉玉麟的函件中提到:
本月初三日英使來部面稱,粵督曾請港督請英政府轉達葡政府禁止澳門賭博,茲奉本國外部電稱,此事應由中政府自向葡政府交涉,英政府可從旁贊助。等語。當經本部電詢粵督,去後。准該督復電稱,本年二月間港督來省,因聞粵有禁賭之事,極力贊成,且稱賭博爲社會製造各項不法媒介,香港及新租界等處彼已飭屬嚴禁,歧並以澳門賭風最盛,中政府如向葡商請禁賭,擬請贊助,港督亦即慨允,屆時當電政府同時提議。查粵自禁賭後,省會賭徒咸往澳門誘人聚賭,且聞葡官有招人勸餉承賭之事,實爲粵人切骨之害。此事已商數月,現港督既已達彼政府,機不可失,請知照駐法劉大臣向葡政府交涉、駐英〔李〕大臣求英政府贊助。[56]
港英當局於1872年1月13日就明示要封閉全港所有賭場,並取消所有開賭牌照,所以在禁賭這方面與清政府並無衝突之處。但是,澳葡政府基於開賭已久,當然不會輕易放棄從稅餉取得的龐大收入。在廣東全面禁賭之際,澳門不但沒有任何配合動作,而且公開招商承充賭餉。
廣東紳民對此極感憤慨,曾專門召集會議商量如何制裁流入內地的澳門私票。[57]但是,隨著辛亥革命的逐步迫近,廣東局勢發生巨變,清政府在廣東禁賭之事也成了明日黃花。繼1911年2月18日開投氹仔番攤,[58]6月14日,澳葡當局對“番攤”、“山票”及“白鴿票”等賭博進行招標之後,[59]同年7月15日公開招商承充“澳門番攤”,底價60萬元,爲期五年;[60]8月,澳門開投番攤賭餉,吸引了一百餘人到場。經過一番角逐,最後由賭商林讓以六十萬零五百元中標。[61]11月25日以封固暗票出投形式,招商承充“澳門、氹仔、路灣山票、白鴿票生意”,以五年爲期;12月2日,澳葡政府又頒佈了“承充澳氹路白鴿票及山票生意實合同之章程”。[62]12月4日招商暗票承充“澳門、氹仔、路灣闡姓生意”,以三年爲期。[63]同年,澳門的番攤博彩毛利達四十五萬元,保持上一年度的水準。澳門市政廳從番攤毛利中抽取2﹪的稅項,也有9000元之數。澳門市政廳從白鴿票抽取的稅項有2381.21元,鋪票稅收為282.5元。[64]這些都是專營壟斷化帶來的好處。經過多年的粵澳兩地反復挪動,賭商對於在澳門經營賭業已有經驗和信心,他們能夠以這樣高的價錢承充番攤等賭館,當然就有把握從中賺取更大的利潤。此時,賭商蟻聚澳門,澳葡政府根本不理會廣東的事情,只顧坐收其利矣。
辛亥革命之後,由於賭博禍害社會頗深,引起内地各省的強烈反感。民國初年,幾次聲勢浩大的禁賭運動,如上海各界的禁彩票運動、廣東的拒賭運動及其他各省的禁賭活動,都是廣大人民群衆推動起來的。可是,另一方面因戰亂迭起,社會經濟遭受到極大破壞。各地軍閥爲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紛紛募兵添械,在掠奪無著的情況下,就把賭捐賭餉作爲重要的收入來源。
在胡漢民、陳炯明督粵時期,曾嚴格禁止山票、鋪票。“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勢力退出廣東,北洋派的龍濟光督粵,諸禁廢弛,禁賭也就成爲一紙空文。1914年,龍濟光與廣東巡按使李國筠藉口救濟廣東水災,招商承餉開辦山票、鋪票,並美其名曰“水災有獎義會”,年餉80萬元,這是民初廣東開賭的先聲。[65]沒過多久,白鴿票也得以死灰復燃。從此,廣東全省“日賭夜賭,鄉賭城賭……無一地不睹,亦無一時不賭”。[66]1917年,桂系軍閥治粵期間曾設籌餉局,再馳賭禁並招商辦捐。第二年時,廣東已有省垣、潮汕、欽廉等三個籌餉局。[67]1920年至1921年陳炯明在廣東主政期間,採取強硬的禁賭政策,山票、鋪票和白鴿票一度被禁絕。不過,隨著滇桂軍進入廣州,山票、鋪票和白鴿票又再度恢復,甚至還出現專門承辦白鴿票的公司。
民初廣東禁賭,無論是認真或是有名無實,對澳門博彩業都已起不到關鍵性的作用。在這段時期,由於大部分賭商已經分別在澳門和廣東開設店號,廣東省的風聲不對,就轉往澳門繼續經營。所以,廣東的禁賭和開賭,對澳門的博彩業已不再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了。
小結
本文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香洲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民初廣東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的考察,充分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後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博彩業與粵港兩地博彩業早期關係為“此興彼衰”,澳門博彩業較大程度上受到粵港兩地政府弛禁賭博政策的影響,甚至兩地的賭博政策關乎澳門博彩業的生死命運。而到了民國初期,由於大部分賭商實行狡兔三窟的策略,分別在澳門和廣東開設店號,廣東省的風聲不對,就轉往澳門繼續經營,極大地降低了開賭館的風險,此時的澳門博彩業則為較少受到或不受粵港兩地賭博政策的影響——廣東的禁賭和開賭,對澳門的博彩業已不再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澳門政府只等坐收漁利便是了!
[1] João José da Silva, Repertorio alphabetico e chronologico ou indice remissivo da legislação ultramarina desde a epocha das descobertas até 1882 inclusive, Lisboa: Typographia de J. F. Pinheiro, 1904, p. 183.
[2] Boletim of do Governo de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1888-3-15 NO-11, Pagina100: “Receita do ano Economico de 1887-1888.” (h) Estabelecida pelo governador a requerimento dos chinas em janerio de 1847. (i) As Licencas para as jogo Foram estabelecidas em abril de 1849 em virtude da portaria de 16 de fevereiro de 1846. 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90頁。
[3]《申報》1880年8月1日,《論賭稅》。
[4]《明清時期澳門檔案文獻資料彙編》(三),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頁《記名道府翰林院檢討潘仕釗請變通挽回鉅款以濟要需摺》,光緒十年九月初八日(1884年10月26日)。
[5]《申報》1885年3月20日,《粵海郵音》。
[6]《澳門政府憲報》,澳門歷史檔案館縮微膠捲B.0. 1887-1911。
[7] 文德泉(Manuel Teixeira):《阿爾諾索伯爵筆下的澳門》,載《文化雜誌》1989年第7-8期合刊,第70頁。
[8]《澳門政府憲報》1888年3月21日,澳門歷史檔案館縮微膠捲B.O. 1888. C0690。
[9]《鏡海叢報》1895年10月9日,《官示照登》。
[10]《鏡海叢報》1895年11月6日,《賭場熱鬧》。
[11]《申報》1897年4月23日,《五羊雜俎》。
[12]《清實錄廣東史料》(六),第667頁,《清代廣東開放之租界、租借地、商埠資料》,廣東省地方史誌編委會辦公室、廣州市地方誌編委會辦公室編,1995年8月。
[13]《澳門問題史料集》第872頁,《清季外交史料》(節選);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匯刊,史部;全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編輯出版委員會編,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8年8月版。
[14]《香山旬報》第三十九期,己酉九月初一日《香洲商埠欲弛賭禁之誤想》。
[15]《香山旬報》第八十期,庚戌十一月十一日《伍漢持主張香洲開賭之荒謬》。
[16]《香山旬報》第八十八期,辛亥二月初七日《是否抵拒澳門》。
[17]《華字日報》1909年5月4日《澳人大敘議》。
[18]《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第90頁。
[19]《香山旬報》第三十三期,己酉七月初一日《速香洲埠之成立者葡人也》。
[20]《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第116頁。
[21]《香山旬報》第三十期 己酉六月初一日《澳門地方稅之窘狀》。
[22]《華字日報》1910年3月22日。
[23]《香山旬報》第九十一期,辛亥二月二十八日《粵督到自治研究社討論禁賭》。
[24]《香山旬報》第九十一期,辛亥二月二十八日《粵督到自治研究社討論禁賭》。
[25]《澳門專檔》(二),第689頁,宣統三年六月初九(1911年7月4日)《外部發粵督張鳴岐電》。
[26]《香山旬報》第一百零三期,辛亥五月二十四日《禁絕澳門賭業之希望》。
[27]《澳門專檔》(二),第690頁,《外部發駐法兼使葡國大臣劉式訓駐英大臣劉玉麟電》,宣統三年六月十一日(1911年7月6日)。
[28]《香山旬報》第九十三期,辛亥三月十三日《張督對於澳門賭博的辦法》。
[29]《香山旬報》第九十五期,辛亥三月二十七日《擬嚴辦澳門賭匪》。
[30]《申報》1911年3月19日,《葡人干預內地禁賭之一斑》。
[31]《香山旬報》第七十一期,庚戌八月十一日《香洲埠竟有鬥蟀演戲開賭之事耶》。
[32]《香山旬報》第八十三期,庚戌十二月十一日《劄查香洲埠商被控告節》;《香山旬報》第九十九期,辛亥四月二十五日《照錄恭都紳商指攻香洲埠商原函》。
[33]《清實錄•宣統政紀》卷47,第835-836頁,(宣統三年辛亥正月丁亥十七日,1911年1月17日)。
[34] 邢永福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十),第6245—6246頁,中國書店2002年7月版。
[35]《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十),第6246頁。
[36]《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十),第6259-6260頁。
[37]《清稗類鈔》第十冊,第4910頁《廣州有番攤館》。
[38]《清實錄•宣統政紀》卷33,第583頁,(宣統二年庚戌三月丁未初三日,1910年4月12日)《都察院代遞廣東京官胡蓉弟等呈》。
[39]《清實錄•宣統政紀》卷38,第674頁,(宣統二年庚戌七月庚戌初九日,1910年8月13日)。
[40]《清實錄•宣統政紀》卷41,第734-735頁(宣統二年庚戌八月癸已二十二日,1910年9月25日)。
[41]《清實錄•宣統政紀》卷42,第763頁(宣統二年庚戌九月庚申二十日,1910年10月22日)。
[42]《清實錄•宣統政紀》卷44,第792-793頁,(宣統二年庚戌十一月癸卯初三日,1910年12月4日)。
[43]《清實錄•宣統政紀》卷45,第812頁,(宣統二年庚戌十一月己已二十九日,1910年12月30日)。
[44]《清實錄•宣統政紀》卷46,第817頁,(宣統二年庚戌十二月壬申初二日,1911年1月2日)。
[45]《清實錄•宣統政紀》卷47,第841-842頁,(宣統二年庚戌十二月辛卯二十一日,1911年1月21日)。
[46]《清實錄•宣統政紀》卷57,第1022頁,(宣統三年辛亥閏六月庚戌十四日,1911年8月8日)。
[47]《華字日報》宣統二年7月5日,《酒米行反抗酒捐》。
[48]《華字日報》宣統三年1月29日,《酒米店罷市之小風潮》。
[49]《華字日報》宣統二年10月25日,《行商大集總商會斥逐區贊森並籌議禁賭情形》。
[50] 何漢威《清末廣東的賭博和賭稅》,第539頁。
[51]《清實錄•宣統政紀》卷57,第1028-1029頁,(宣統三年辛亥閏六月戊午二十二日,1911年8月16日)。
[52] 何漢威《清末廣東的賭博和賭稅》,第539頁。
[53]《清宣統實錄》卷57,第1032-1034頁。
[54]《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四),第701頁,宣統三年六月初四日(1911年6月29日《兩廣總督張鳴岐爲澳門禁賭請電劉式訓與葡交涉並請英政府設法贊助事復外務部電文》。
[55]《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四),第701-702頁,宣統三年六月初四日(1911年6月29日)《兩廣總督張鳴岐爲澳門禁賭請電劉式訓與葡交涉並請英政府設法贊助事復外務部電文》。
[56]《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四),第706-707頁,宣統三年六月十一日(1911年7月6日)《外務部爲請商葡政府轉飭澳督禁賭並密商英政府設法幫助事致駐法兼使葡國大臣劉式訓等函》。
[57]《申報》1911年7月31日。
[58]《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2月18日(第7號)《大西洋澳門督理國課羅(Manual Fortera da Resha)出示招投事》。
[59]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第55頁。
[60]《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7月15日(第28號)《大西洋澳門正督理國課官田爲通知事》。
[61]《華字日報》1911年8月14日《澳門投賭》。
[62]《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12月2日(第48號)《承充澳氹路白鴿票及山票生意實合同之章程》。
[63]《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11月18日(第46號)《大西洋澳門國課官田爲通知事》。
[64]《澳門政府憲報》,澳門歷史檔案館B.O.1912.
[65] 廣州年鑒編纂委員會編:《廣州年鑒》第21卷,民國二十三年版,《廣州大事記》,第2頁。
[66]《粵省新聞》,香港《華字日報》1915年3月16日。
[67]《粵省新聞》,香港《華字日報》1918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