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朝初建之时,明太祖多次遣使赴日,欲以通好。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派遣赵孟頫后人、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等人赴日。为给日本增加更大的外交压力,明太祖又派遣杨载第二次赴日,负责押送15名倭寇。最终,怀良亲王遣使来华朝贡,奉表称臣。怀良态度的陡转并非仅仅由于赵秩庭上的激昂陈词,而是与其面临的北朝大敌压境的客观形势有关。四年,赵秩并没有继续客留日本,而是回到了明朝。赵秩第二次出使日本时与仲猷祖阐、无逸克勤等人同舟,时值五年五月末,而非如《明实录》等所记载之四年十月。洪武六年十月至次年五月,赵秩等人之所以在博多长久停留,是因需候风等船,他们并没有被当地官员拘留,相反,在此期间他们与日本友人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且得到了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
关键词:中日关系 赵秩 杨载 怀良亲王 倭寇
责任编辑:潘清
作 者:马光,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 刊:《江海学刊》2020年第2期,第173—183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ZS052)、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PDF文档:CNKI官网
全文版本:《江海学刊》官方公众号
以下文字为初稿,未经编辑,非正式版。正式引用,请参考PDF。
赵秩,自称为元代著名书法大家赵孟頫(1254—1332)“松雪公孙”,明初曾以山东莱州府同知身份赴日,成功促使当时处于窘境的日本怀良亲王改变敌对态度,转身决定遣使赴明朝贡,从而首次打破自元代忽必烈东征日本之后中日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外交僵局,开启了两国外交新局面。然而,与赵秩的重要功绩相比,现存中国史籍中有关赵秩赴日活动的记载却极为匮乏,由此造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赵秩在日本的活动语焉不详,甚至还存在诸多误解。
明初中日外交史因其承前启后的重要性,多为学者所关注。自上世纪初至今,不少中外学者都对之有过专门研究,其中包括对赵秩问题的探讨。[①]这些研究成果,无疑给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外学术界对赵秩赴日活动的研究中,至今仍存在一些具有争议或解读有误的问题。比如:赵秩是洪武三年还是四年赴日?他在洪武四年是随日本使团回国还是客留在了日本?怀良亲王向明朝称臣纳贡是事实还是伪史?赵秩、仲猷祖阐、无逸克勤[②]等人是洪武四年还是洪武五年使日,他们是否同行,为何在博多停留那么久,是否受到了怀良亲王或当地官员的拘留或监视?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发掘新史料、重新解读旧史料,对明初赵秩赴日问题提再进行深入探讨。不当之处,还请方家赐教。
一、失败的外交破冰之旅
明洪武初期,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频繁,沿海居民甚受其扰。[③]是时,国内形势仍不稳定,元朝残余势力依然盘踞北方,云南、四川、东北等地尚未完全统一,张士诚(1321—1367)、方国珍(1319—1394)等部残余势力不断骚扰沿海地区,余党也多逃亡海上,在沿海地区“焚居民,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④]因此,明政府此时并不能投入大规模的人力与物力去加强沿海军事力量以防止倭寇的侵扰,故多依赖外交与祭神等消极措施。
继位之初,明太祖对日本抱有很大幻想,欲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政府禁倭,以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故而积极主动地展开了“倭寇外交”。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明太祖“遣使颁诏报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各四夷君长”,传达了明王朝欲与诸国通好的信息。[⑤]洪武二年二月,占城入贡。[⑥]六月,安南入贡。[⑦]八月,高丽入贡。[⑧]然而,日本却迟迟未派遣使团来华。是为何故?原来明太祖第一次派遣到日本的使者在到达日本境内之后,不幸被贼所杀。[⑨]据仲猷祖阐、无逸克勤致天龙寺方丈清溪通彻的书信记载:
首命使适日本通好,舟至境内,遇贼杀,杀害来使,诏书毁溺。寻有岛民,逾海作寇,数犯边卤,多掠子女。皇帝一欲通两家之好,悉置而不问,但令自禁之。故后复两遣使来,谕以此意,俱为镇西所沮。[⑩]
由此可知,洪武元年派出明朝使者刚入日本境内即被贼所害,诏书毁溺,自然也就谈不上见到日本怀良亲王等人了。明朝与日本的首次外交以中途失败而告终。[11]
面对沿海日益严重的倭寇问题,明太祖不得不于洪武二年二月再次派遣行人杨载、吴文华等七人出使日本。[12]明太祖在国书中明确提到山东所遭受的严重倭患,要求日本政府配合明朝靖倭,严格管束臣民,禁止匪寇到中国沿海地区寻衅滋事:“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13]从中可以看到,明太祖对倭寇问题极为重视,并扬言若日本再纵民为寇明朝将扬帆进攻日本。
杨载一行抵达日本后,见到的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南朝的怀良亲王。九州等地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最为接近,航行颇便,故南朝政府成了明朝使团所到之地。[14]作为后醍醐天皇(1318—1339在位)的儿子,怀良是日本南朝政府中的关键人物。1336年,后醍醐天皇为压制足利尊氏的势力,任命怀良为征西大将军,据守四国伊予国的忽那岛(今爱媛县松山市)。1348年,怀良在肥后国隈府(今熊本县菊池市)建立征西府,与此同时,室町幕府则在博多设立镇西总大将一职,与南朝对峙。1359年,南朝军与幕府军发生筑后川之战。南朝获胜,从而赢得了之后十年的九州统治权。[15]杨载一行到达日本时,怀良亲王势力正盛。诏书中,明太祖的那种颐指气使的天朝大国心态一览无遗。怀良见此诏书自然是勃然大怒,遂斩五个明使,并将杨载、吴文华二人拘囚起来,三个月后才让他们回国。[16]
杨载一行不但没能使日本臣服,反而激怒了怀良,致使来使被斩、被囚,大国颜面尽失。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倭寇一事自然也是告吹,倭寇再次“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17]

二、赵秩首次赴日与怀良称臣
杨载出使日本失败之后,明太祖并不甘心。面对沿海的倭寇问题,时隔一年,洪武三年,明太祖又派遣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等人持诏谕日本国王。[18]为了给日本增加更大的外交压力,明太祖又派遣杨载押送15名倭寇赴日。最终,迫于内外形势压力,怀良亲王派遣使团来华朝贡,奉表称臣,开启了两国通交的新篇章。
囿于史料,之前学者对赵秩本人的生平所知甚少,故在此我们需要对他多一些着墨。赵秩,字可庸,号啮雪、啮雪子、啮雪老子、鳄水、石门渔者等。关于赵秩籍贯与身世,他曾自称“松雪公孙吴兴赵秩可庸”、“松雪公孙赵可庸”、“啮雪子赵秩”、[19]“大明天使松雪余芳王孙赵别驾”、“啮雪子古霅赵秩”、[20]“啮雪老子赵可庸”。[21]“松雪公”指赵孟頫,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鸥波,宋元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系子孙。“古霅”指吴兴,因其境内有霅溪而得名。由此可知,赵秩当为吴兴赵孟頫后代。然而,元末明初著名诗人王逢(1319—1388)称赵秩为括苍人。[22]赵秩曾自题“前隐士石门渔者赵可庸”,[23]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他为今桐乡市石门镇人,或为杭州钱塘人。[24]之所以会出现吴兴、括苍、钱塘、石门等不同情况,笔者认为,吴兴为其祖籍地,而钱塘、括苍等地可能为其迁居地。
《明太祖实录》称赵秩为“莱州府同知”,然而,根据《莱州府志》记载,明初莱州府同知为刘元俊,洪武三年任。之后为姚文临,十年任;郑亨,十五年任。[25]据此,似乎可推断赵秩并非莱州府同知。赴日期间,赵秩曾自称“别驾”,日僧春屋妙葩(1311—1388)等人在唱和诗文中也称他为“大明天使赵别驾”、“可庸别驾”、“赵别驾可庸”。[26]别驾通常指通判,而非同知。查《莱州府志》,洪武三年至八年,莱州府通判一职有李毅、谢得仁、陈承务、陈士贤等相继就任,同样也没有赵秩。[27]笔者近年来曾访查赵孟頫宗谱和碑铭等相关资料,然而迄今为止,并未发现任何有关赵秩的记载,其身世待进一步考证。[28]
关于赵秩的年龄,目前所见资料十分有限。赵秩在日本期间曾多次作诗提及自己的“白发”:“霜雪布袍成潦倒,功名白发自咨嗟”,[29]“未归行色客愁添,白发功名岁月淹”。[30]由此可知,此时他已两鬓斑白,当为中老年人了。日本山口县立山口博物馆和毛利博物馆各藏有一套《寿老花鸟图》三幅对,居中一幅有“辛巳之春日写于鸿城客舍以寿萍水园主人百岁钱塘赵秩”的题款。学者多认为辛巳年应为1401年,且推测题款者即为洪武出使日本的赵秩。[31]若推断正确,那么说明1401年赵秩依然健在。目前,日本还现存赵秩所画的另外一套《关羽画轴》,卷轴上有“赵秩可庸画”,内有“赵秩”题款。至于这三套画作如何流传到日本,仍是谜团。
关于赵秩首次出使日本的时间,目前学术界多认为《明太祖实录》中所记载的洪武三年三月较为准确。然而,查阅其它史籍,至少还有另外两种说法,即洪武二年说与洪武四年说。通过《明太祖实录》、明人文集等文献我们可以断定洪武二年赴日使者为杨载等人,非赵秩一行,所以洪武二年说站不住脚,故我们来重点分析洪武四年说。[32]《明太祖实录》中虽然直接记载洪武三年三月“是月,遣莱州同知赵秩持诏谕日本国王良怀”,[33]但是三月是谕令下达的时间,考虑到使日需要一定的准备过程,所以该月可能并非实际的出发时间。据《国朝典汇》载:
三年三月,遣莱州同知赵秩持诏谕日本国王良怀……四年,赵秩等往日本,泛海至析木崕,入其境,关者拒勿纳。[34]
从中可以看出,书中记载洪武三年三月明太祖下令派遣赵秩持诏书至日本,而直到次年赵秩才前往日本。若没有一定依据和把握的话,作者应该不会专门在同一处强调诏令的下达时间与实际出发时间的不同。明代其它史籍,如《皇明象胥录》、《新刻明政统宗》、《殊域周咨录》、《文直行书》、《国朝武功纪胜通考》、《两朝平攘录》等亦多言赵秩是在洪武四年使日。[35]
在赵秩所携带的给日本的国书中,明太祖提到“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即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36]考诸史实可知,洪武三年六月遣使持诏谕爪哇、西洋琐里等国,[37]两国分别于当年九月、十月首次称臣入贡,[38]国书中所载内容当为已发生之事,据此推断,赵秩应在十月之后才出发。[39]
 图 1 寿老花鸟图[40]
图 1 寿老花鸟图[40]
 图2 寿老花鸟图[41]
图2 寿老花鸟图[41]
-1.jpg) 图 3 关羽画轴[42]
图 3 关羽画轴[42]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方面的相关记载。据日本史籍《櫻云記》载:建德二年(应安四年,1371)二月,怀良在接到大明国书后进行回信,信中自称“日本国王怀良”,同时他下令制造大船,准备派遣使团赴明。[43]《菊池家代々記錄》也记载:应安四年,大明使者赵秩到达日本,见到怀良亲王之后,怀良答复国书,并命令菊池武光的嫡子护送如瑶藏主等前往大明。[44]由此可知,洪武四年二月左右怀良亲王下令造海船以遣使到明朝,此时应该是怀良见过赵秩不久。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再结合《国朝典汇》等资料的记载,那么我们可以判定赵秩应该在洪武四年正月或二月到达日本。然而,因相关资料的匮乏,我们只能推测到此。若想判断赵秩首次使日的确切时间,需要发掘更多的资料。
赵秩一行不畏艰险终于抵达日本析木崖,但是却被守关者拒之关外,于是赵秩遂将国书传达给怀良亲王。在国书中明太祖首先表明自己继位是“荷上天祖宗之佑”,表明其合法性,然后又指出高丽、安南等周边国家多已顺天奉命,称臣入贡,唯独日本不但没有来华朝贡,反而纵民为寇,骚扰中国沿海:
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45]
明太祖还提及他曾欲命令将士“整饬巨舟”,进攻日本,后因从被捕的倭寇口中得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所以才暂停造舟,改派使者赴日再次交涉。
据《明太祖实录》等载,怀良初见赵秩,以为赵秩是蒙元赵姓使者的后代,误认为明朝又会像元朝那样故伎重演,表面上遣使通好,暗地里却准备进攻日本,故“命左右将刃之”,而赵秩却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据理力争,称明朝乃华夏正统,非蒙古戎狄可比。怀良听闻之后遂“气沮,下堂延秩,礼遇有加”,之后奉表称臣,派遣祖来等人随赵秩到中国朝贡。[46]
然而,《明太祖实录》对赵秩不辱使命的外交抗争描述得极为生动,甚至有些夸张,这就不免有些令人生疑。正如上文所述,怀良之前已经见过杨载等人,应该对元亡明兴的朝代更替之事极为清楚,且明太祖在这次的诏书中再次十分明确地提到“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47]所以怀良应该不会误将赵秩当作元朝使者而对待。杨载与赵秩所持的两封诏书皆言辞犀利,盛气凌人,怀良既然上次敢杀来使,断不会因为赵秩的一番据理力争就轻易改变其原有强硬的敌对态度。怀良之所以转而决定对明朝俯首称臣,其实应该是迫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压力。前文提到,杨载一行到达日本时怀良势力正盛,故怀良无所忌惮,敢杀来使,拒绝与明通交。然而好景不长,南朝政府不久便由盛而衰,危机重重。彼时,怀良的压力主要来自实力强劲的室町幕府大军。1370年被足利义满将军(1358—1408)正式任命为九州探题后,能征善战的金川了俊(1326—1420)便召集毛利元春、吉川经见等各方力量准备讨伐南朝。怀良得知各方劲敌准备联合讨伐他时,岂能坦然处之?此时,恰逢明朝来使,于是怀良便趁机一改去年之敌对态度,转对抗为恭顺,甘愿俯首称臣,欲借明朝声势来抵抗各方压力。[48]
事实上,促使怀良改变其立场的还有一个常被学者所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明太祖再次派遣杨载出使日本向其施加外交压力。据明代史家高岱(1508—1564)记载,赵秩见到怀良,经过一番雄辩之后,“日本国王气沮,会上复遣杨载往,于是日本王良怀礼遇载等有加,遣其陪臣并僧九人随诏使入朝”,奉表称臣。[49]从中可以看出,曾出使过日本的杨载又被派遣赴日,并且连同赵秩一起向怀良施压,终于迫使怀良决定遣使来华。
杨载再次使日一事并非仅见于高岱《鸿猷录》,清万斯同(1638—1702)《明史》与王鸿绪(1645—1723)《明史藁》等也载“又有杨载者,尝官行人,凡再使日本,还,复使琉球”。[50]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胡翰(1307—1381年)在《赠杨载序》中也曾提到: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师,会杨载招谕日本,自海上至。未几,诏复往使其国。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贡,载以劳获被宠赉,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从载入贡。道里所经,余复见于太末,窃壮其行。[51]
由序文可知,洪武二年,胡翰客留南京期间正好遇到杨载从日本回国。不久,杨载又再次被派遣至日本。洪武四年,日本遣使随杨载等人来华,杨载因功而受厚赏。胡翰,字仲申,号仲子,金华人。作为同时代的人,胡翰至少见过杨载两次,一次是在南京,一次是在太末,且胡翰又专门赠文给杨载以“壮其行”,所以两人应该是相当熟稔的朋友,故其所记内容无疑具有较高可信度与权威性。
然而,这几则史料对杨载此次出使的具体目的却缺乏相应的详细记载。所幸的是,洪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明中书省给日本的一份咨文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适被杀死五人,杨载、吴文华羁留三月,方才得回。开谕一节,略不见答。又况使者未回之时,海内人船,仍前出没劫掠,及有僧人潜为奸细,俱已擒获。……为此都省令差宣使杨载等,伴送灵南、阳谷等一十五名前去,令行移咨,请照验施行。[52]
由此可见,杨载第一次使日受挫回到中国之后又被中书省再次派遣使日。杨载此次主要负责押送灵南、阳谷等被捕的倭寇前往日本,要求日本政府严肃处理并以之为戒。咨文和胡翰序文等文献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杨载见到了怀良,但是联系高岱所记内容及怀良于洪武四年遣使来贡的史实可知,杨载第二次使日应该就是去见的怀良。他所押送回去的十五个倭寇无疑给怀良以政治压力,是成功促使怀良来华的一个重要因素。
洪武四年十月,怀良亲王遣祖来、如瑶等来“随秩入贡”,[53]“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明太祖对日本来朝大喜过望,遂厚待来使,赐怀良《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54]
怀良在呈给明朝的表笺中自称“日本国王”。[55]表文是起源于汉代的一种上行文种,用于臣僚向君主陈述政事,表达情感。在明代,凡遇朝廷举行庆典,如寿旦、元旦、冬至等,文武百官都要照例进贺“表”(用于皇帝和皇太后)、“笺”(用于皇后)。同时,明朝也规定外国来华必须进奉表文,“四夷入贡中国,必奉表文”,以表示他们对中国政治上的臣服与隶属,否则,明朝便会“却其贡献”,甚至与之断绝外交。[56]怀良向明朝“进表笺”,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俯首称臣。然而,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所谓的奉表称臣一事,从亲王的一贯态度来推测,似乎是不可能的。或许由于起草公文的僧侣信笔写成这样,也许只是《明史》撰者的润色之词。”[57]但是,木宫泰彦的观点没有任何的文献依据,纯属猜测,缺乏说服力。为了弄清此事,我们来看一下当事人的相关记载。宋濂在《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中写道“日本良怀亦令僧祖来奉表而至,上嘉其远诚,诏以天宁禅僧祖阐、瓦官教僧克勤为使,护其还国。”[58]序中明确指出怀良亲王是“奉表而至”。临济宗名僧、天界寺住持宗泐(1318—1391)也曾在送祖阐、克勤的送行诗中写道:“维彼日本王,独遣沙门至。宝刀与名马,用致臣服意。天子钦其衷,复命重乃事。”[59]诗中明确指出“日本王”即日本国王派遣僧人作为使者来华贡献宝刀、名马等方物,以表称臣之意。作为当事人,宋濂和宗泐无疑非常了解此次日本来使的一举一动。序文和送行诗都是作给当时朋友看的,完全没有必要矫饰欺人,故他们的记载是最为可靠的史料,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再者,前文所引胡翰给杨载的序文中提及“日本奉表入贡,载以劳获被宠赉”,同样表明日本曾奉表称臣。[60]所以,笔者认为当时怀良来华应该是奉表称臣纳贡,不然明太祖断然不会欣然接受使团,厚赐来使,也不会专门遣使护送他们回国。
三、赵秩是否回国?
关于赵秩随日本使团于洪武四年回国一事,《明太祖实录》明确记载怀良“遣祖来随秩入贡”,所以学者通常认为赵秩是同怀良使团一同回国的。然而,日本学者村井章介对此持有不同意见。通过整理《云门一曲》等文献,村井发现赵秩与日僧春屋妙葩等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并且他曾在诗文中多次提及自己客居日本三年。由此,村井章介推断赵秩并没有像《明太祖实录》等所记载的那样于洪武四年十月随日本使团回国,而是客留在了日本,直到洪武七年,赵秩才与祖阐等人一同返回中国。[61]村井章介关于赵秩客留日本的新观点对旧有“定论”无疑具有极大冲击性,不少学者甚是赞同此新说。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新说同样值得商榷。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赵秩等人的诗文中出现的“三年”一词——这是村井章介立论的重要依据。翻阅《云门一曲》,我们会发现赵秩及其同行者朱本等人在洪武六年十月至洪武七年的四月期间所作的诗文中时常出现“三年”、“三岁”、“三载”等词。比如“远客三年衣锦归,海上峰峦红日近”,[62]“三年持节石城头,偶到周防得胜游”,[63]“余奉使日本三年矣,雅与方外交游者,而声出为诗者有之,而高卓奇特者鲜矣”,[64]“奉使日本来复三年,未尝有慷慨知人重贤中礼节者似尊师之模范也”,[65]“仆远来万里,旅泊三年,五节固持,安贫自守,为我心忧者,惟老师一人”,[66]“三年筑国望丹丘,欲上丹丘恨未由”,[67]“三年尘镜人容老,几夜吟窗月影西”,[68]“雁外一缄披尺帛,客中三岁咏千秋”,[69]“三年逆浪仙槎月,应向吴江照梦魂”,[70]“歌宴皇华酒几添,三年守节未为淹”,[71]“三载丹丘共缔盟,今春何事独西行”。[72]
根据诗文中出现的这些“三年”,村井章介推断赵秩洪武四年并没有回国而是一直客留在日本。然而村井章介没能解释这样一个问题:若从洪武三年算起,至洪武六年是“三年”,至洪武七年则是“四年”,但是为何诗文中没有使用“四年”一词呢?对此,年旭认为对不同年份诗文中的“三年”应采用不同的时间计算起点,即:洪武六年诗文中的“三年”应从洪武三年算起,而洪武七年诗文中的“三年”则应从洪武四年第二次赴日算起。[73]这种解释显然值得商榷。其一,赵秩、朱本等人不可能在短时间(约半年)内对出使日本一事使用不同的计算起点,即不可能说洪武六年十月诗文中以洪武三年使日为计时起点,而洪武七年三、四月又以洪武四年第二次使日为计时起点;其二,赵秩第二次赴日并不是在洪武四年,而是在洪武五年。这一点可以从朱本在回忆洪武六年之事的序文中得到确证:
使日本之明年,将归朝,会前天龙堂上春屋葩公大禅师命其徒周允上人自丹丘远来石城,通书问道殷勤。[74]
结合行文背景可知,序言中的“明年”指的是洪武六年。是年,祖阐等人见过足利义满之后,于秋天去博多候风准备回国,而赵秩、朱本听闻消息之后也赶到博多准备同船归国。由此推断,赵秩、朱本等人使日是在洪武五年,而非洪武四年。所以,若将洪武七年所作诗文中的“三年”的时间起点理解为从洪武四年开始显然从根源上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这些诗文中的“三年”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笔者认为,这些诗歌中的数词应该多是虚指。众所周知,古代诗歌中的数词有实指和虚指之分。为了讲求意境美和韵律美,数词虚指现象比较普遍,三、六、九、十、百、千、万等数词更是常用来表示虚指。例如,“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烽火连三月”,“飞流直下三千尺”等中的“三岁”、“三月”、“三千”等均是虚指,不能理解为实指。[75]赵秩等人诗歌中的“三年”应该多是虚指,而非实际的三年时间。“三年”系虚指也可以从克勤的诗歌中得以证实。例如“莫怪多情王粲赋,三年隔海望长安”,[76]“丹后高居我所思,三年不见共幽期”[77],这些诗文均为克勤在洪武六年九月至次年三月间所作。克勤是洪武五年五月底才抵达日本(详见下文),即使是到洪武七年四月,他在日本所停留的时间也不足两年,故何来“三年”之说?所以,克勤诗文中的“三年”应该也是虚指。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为讲求意境美与韵律美,赵秩、朱本、克勤、春屋妙葩等人所作诗歌中“三年”应该多是虚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数词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是实指,也不能完全把它当作十分精确的现代意义上的计时概念来逆推使日时间,即不能把“三年”严格限定在25个月至47个月之间,否则逆推出来的结论便会有悖于史实。因此,在考证确切使日时间时,以上诗文中出现的“三年”只能当作一种模糊的时间段来参考,而不能将之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三年”。
村井章介同时还提及了另外一组文献:洪武三年明中书省给日本国王的咨文、洪武五年九月克勤致天台座主和洪武六年八月左右祖阐、克勤致天龙寺住持的书简,令人称奇的是他们曾共同保存在北朝睿山。
为何这三份不同年代的文献会在一起保存呢?村井章介认为赵秩一直客留日本,等祖阐、克勤等人到日本之后,赵秩与两僧相见,并将之前的咨文转交给两僧,然后两僧又将国书连同书简一起送至北朝。年旭则认为几种年代不同的文件在一起保存的可能性有很多,比如北朝攻陷南朝后将赵秩的咨文连同祖阐、克勤致北朝僧人的书简一同带到了北朝保存,或赵秩于洪武三年使日时除诏书外还带有两份咨文,其中一份递交给了南朝,另一份则因阻未到北朝,等其回国后与两僧再度使日时又将咨文再次递送。[78]以上种种解释和猜测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缺乏相应的史料支撑。笔者认为明中书省的咨文并非由赵秩负责。从咨文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以明中书省而非明太祖的名义给日本国王的文件,故采用的是通常用于同级交流的咨文而非玺书。由“都省令差宣使杨载等,伴送灵南、阳谷等一十五名前去,令行移咨,请照验施行”一句可知,咨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日本严惩这些倭寇并禁倭,而担负这一使命的为中书省派出的杨载,故递交人应该是杨载而非赵秩。[79]
综上所述,上述诗文中“三年”一词系虚指,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时间数词。村井章介对“三年”一词的不当解读,导致他误认为赵秩在洪武三年到达日本后,并没有于洪武四年随日本使团回国,而是一直到洪武七年才回国。其实,赵秩完全有可能在洪武四年回国,然后再次赴日后客留到洪武七年再回国。下面我们继续探讨赵秩第二次使日的可能性。
四、赵秩是否再次赴日?
赵秩到底是否曾经两次使日?赵秩曾在致日僧春屋妙葩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奉使日本来复三年”,[80]这说明他不止一次去过日本,但是没有具体指明去过日本几次。王逢所作的《题括苍赵秩可庸两使东夷行卷》为解答赵秩使日问题提供了最直接、最明确的证据:
维日本启国曰卑弥呼氏,始觐桓帝朝,乃冠带理。爰至唐宋,若父母抚子。有元征不庭,由行人匪贤,或梗或通,垂八十年。明君作,远用柔,表降贡违,厥臣仆羞,君其韬威,秩是谋。再诏秩往僧[81]同舟,鼓铙轰震龙伏湫。旌幢电晔香雾浮,弥月说法飞梅陬。名王恭迎驾象辀,秩也徐策天驷骝。仁义汉节,诗书吴钩,掠躭罗,观毛人,宠扶桑,驻流求。阳舒阴翕上德意,冒岚冲涛百艰勚。绣衣经寒紫贝阙,骊珠呈春白玉陛。收名汗竹光汴裔,折丕赵咨乌并辔。[82]
王逢这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珍贵信息:首先,他在题目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赵秩曾“两使东夷”,文中又言赵秩的勇谋深得明太祖赏识,故“再诏秩往”;其次,他明确指出赵秩第二次使日时是与祖阐、克勤等人“同舟”;第三,他生动描述了赵秩、祖阐等人在日本的弘扬佛法、诗歌倡和等文化交流活动。
那么,赵秩与祖阐、克勤等人是否真的同行呢?他们赴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看赵秩自己的表述。洪武七年三月赵秩在给日僧的一篇序文中提及:
余天子知日本尚佛法,故命有德行天宁禅师、瓦官讲师奉使辟扬佛教,遣余辈谕毛人,同其来。二师面王陈法,王谓日本、毛人一体,使祖公复命天子,同使僧、使官归朝。[83]
从中可以看到,此次使日,祖阐、克勤主要奉命宣扬佛教,而赵秩等人则“同其来”,奉命告谕毛人。两僧与赵秩使日的具体分工虽然不同,但都是属于同一使团,故一起同行。
再来看《智觉普明国师语录》中的记载:
门人编曰《云门一曲》,大明国使赵秋[84](可庸)、朱本(本中)[85]题其序跋。时赵、朱二公馆防之大内,与丹阳相去十数日程。虽然修途艰险,书问来往六七回。又天宁阐仲猷、瓦官勤无逸,奉使同来,侨于博多。[86]
该书是春屋妙葩众弟子整理、编写的有关春屋妙葩事迹的作品。春屋妙葩,日本临济宗僧,自号不轻子,曾任天龙寺住持。洪武六年秋至次年春期间,春屋妙葩及其众弟子与赵秩诗文往来十分频繁,故彼此之间十分熟稔。据此书可知,赵秩、朱本与祖阐、克勤两僧的确是“奉使同来”。
以上材料只是表明赵秩与祖阐等人同行,但是却没有记载他们一同出使日本的具体时间。古今不少学者认为祖阐、克勤一行到达日本是在洪武四年,[87]其主要依据是《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十月癸巳”条的记载:
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比辞,遣僧祖阐、克勤等八人护送还国,仍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88]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明太祖实录》之所以将日本使团朝贡、回国一事在同日条下记载,显然是为了叙事的完整,故当日或当月不一定就是使团回日之时。据明代学者薛俊等人记载,洪武五年:
太祖皇帝谓刘基曰:“东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犹蚊蚤警寤,自觉不宁。议其俗尚禅教,宣选高僧说其归顺。”遂命明州天宁寺僧祖阐仲猷、南京瓦罐僧无逸克勤往彼,化其来贡。[89]
明人著作如《筹海图编》、《海防纂要》等中言祖阐、克勤等人于洪武五年出发,但未提及具体月份。[90]实际上,祖阐等人直到洪武五年五月底才出发去日本。洪武五年九月一日,克勤在给延历寺座主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于五月二十日,命舟四明。三日[91]至五岛,五日而抵博多。上无惊风,下无骇浪,茍余心之不若是,则佛祖神明,宁宜使安固疾速之若是哉。……不意使之留抵圣福,以衣贸食,而翘足待命者百余日矣,而犹窅然未报。[92]
由此可知,祖阐一行是在五月底抵达日本。如上文所述,既然赵秩与之同舟,故赵秩也应是此时抵达日本。祖阐赴日时还有可能负责押送被俘的倭寇。洪武五年初,“倭夷入寇,戍将每捕获之,上悯其无知,命儒臣草诏,归其俘”,礼部侍郎曾鲁(1319—1372)在草诏中因有“中国一视同仁”之语而大受明太祖欣赏。[93]据此可知当年应该有倭寇被押送回日本,而当年赴日的使团只有祖阐一行,故很可能由其负责此事。当然,这种推测有待进一步的史料论证。
赵秩与祖阐同抵日本后,两队人马分头行动。洪武五年冬,赵秩、朱本“欲假道之京洛”,中途在周防停留,在春屋妙葩弟子龙海、玉林的帮助下,住在大内氏馆内。洪武六年夏,赵秩离开周防,但不幸遭遇匪徒打劫,财物尽失,无奈只得回到山口。在山口期间,赵秩与春屋妙葩弟子交流甚多。秋季,赵秩听闻祖阐等人将至博多候风回国,便赶往博多与之会合。[94]
然而,直到次年五月底,一行人才得以从日本出发。从洪武六年秋到七年五月祖阐一行人一直停留在博多,时间如此之长,不禁令人生疑。他们为什么要待这么长时间呢?木宫泰彦认为二僧归国之时,又到征西府聘问,上《大统历》及文绮、纱罗,但是怀良亲王对他们秘密入京一事大为不满,又见所颁示的《大统历》,有使奉正朔之意,故拘留二僧甚久。[95]王伊同猜测祖阐一行在九州可能被当地官员拘留。[96]佐久间重男认为一行人尽管受到监视,但是却伺机颁赐《大统历》给怀良亲王,不过迫于当时日本的动乱形势最终没能达成使命。[97]郑樑生认为明使曾拟将《大统历》交与征西将军府而未被接受。[98]村井章介认为明使到达博多后,在九州探题的监视下一直在妙乐寺候风。[99]陈小法认为因为足利义满的使臣和众多日僧当时是同他们在一起候风,故明使不可能再向怀良亲王颁赐《大统历》,且当时怀良亲王已退居幕后,明使也就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无谓的冒险了。[100]
其实,一行人之所以在博多停留如此长时间,主要是要“见伺风讯”,但遗憾的是“天风未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乘船回国。洪武六年十一月末,赵秩告知春屋妙葩自己即将于次年二月初回国,不料七年二月又因“天风未遂”不能成行,一行人只能继续“再当问讯”。[101]三月,祖阐在送日僧周允上人的信中说“王事纷惚,归期速迫”,所以急盼回国。[102]木宫泰彦等人提出的明使被拘留一说,实为没有根据的猜测。事实上,在此期间,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拘禁,相反,得到了众多日本友人的帮助。比如,春屋妙葩不但给赵秩等人提供“三冬足用衣绵繻布”,而且还赠送盘缠使他们顺利抵达博多。詹征回赠图书、唐笔等以示谢意。[103]纵观祖阐、赵秩等人在此期间与众多日僧的交流活动及其所作的诗文,没有任何线索表明或暗示明使曾被拘留或被软禁。
洪武七年五月底,赵秩、祖阐、克勤等人回国,同行的还有足利义满派遣的以宣闻溪、净业和喜春为代表的官方使团和来中国学习的众多日本僧人,“有僧慕游中国者数百辈,皆俊雅之徒,亦有未及冠年者,咸忻然趋从而往”。[104]顺利抵达中国后,祖阐、克勤二十九日得到了明太祖的接见,因两僧功绩显著,故每人个被赏白金百两,文绮、帛各二匹。[105]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赵秩至少曾两次出使过日本,且第二次出使日本时是与祖阐等人“同舟”而行,同时达到日本,而非如有的学者所推测的分批先后到达。[106]赵秩第二次使日主要是为了告谕毛人,可能还起一定的向导作用。从他书信中提及的“有司不允其行”一句可以推知,此次赵秩只是处于次要地位,非主使。[107]
五、余论
洪武初期,中国沿海屡遭倭患,但因天下初定,明朝并没有太多的军事力量去武力靖倭。明太祖最初对日本抱有很大幻想,欲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靖倭,故而积极主动地开展“倭寇外交”。洪武元年明太祖首次遣使日本,但使者甫入日本境内便被贼所杀。次年二月明太祖又派杨载、吴文华等七人出使日本,但怀良亲王却怒斩明使多人,拘杨、吴三月之久方让其回国,致使明朝颜面尽失。
因沿海倭寇问题依然严重,明太祖不得不再次派遣赵秩前往日本。关于赵秩首次出使日本的时间,目前学术界多认为《明太祖实录》中所记载的洪武三年三月较为准确。然而,应该注意到,实录中虽然直接记载三月“遣莱州同知赵秩持诏谕日本国王良怀”,但这是谕令下达的时间,考虑到使日需要一定的准备过程,所以该月并非实际的出发时间。实际上,赵秩应该直到洪武四年正月或二月才到达日本。《明太祖实录》等书宣称因赵秩的据理抗争方使怀良亲王决定来华朝贡,其实过分夸大了他慷慨激昂的说词,而忽略了其它因素。事实上,当时明中书省还派遣杨载押送15名倭寇再次赴日,要求日本从严处理这些倭寇,这无疑给怀良不小的政治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北朝大军气势汹汹,乌云压境。面临如此困境,为保全自身,怀良亲王不得不改变其原有敌对态度,转而俯首奉表,向明朝称臣纳贡。针对村井章介等人提出的赵秩一直客留日本的“新观点”,本文认为由于对诗歌中“三年”一词的错误理解,导致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事实上,赵秩在洪武四年的确曾随日本使团一同回国,但之后他又于洪武五年五月同祖阐、克勤等人一起同舟,再度赴日,赵秩此次使日主要是为了告谕毛人,可能还起一定的向导作用。直到洪武七年五月才回国。从洪武六年十月至次年五月,赵秩一行之所以在博多待如此之久,是因为季风不顺,没有合适的渡船机会。有学者认为在此期间他们见了怀良亲王,或推测他们曾被拘留或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事实上,赵秩一行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见怀良亲王,也没有被当地官员拘留,相反,在此期间他们与日本友人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且得到了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
由上观之,明初中日关系史虽经数代名家耕耘,拙文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做了一些细小的推进工作,然而至今为止,仍有不少的谜团,例如:赵秩生于何时,卒于何年?他是莱州府同知还是通判?为何他的任职信息不见于地方志?赵秩外交有功,理应升迁,为何不见其它记载?他真是赵孟頫的后代吗?若是,那么是直系后代还是旁系后代?他在辛巳(1401)之春作的几幅画,是真是假,又如何流传到日本?洪武五年,负责押送倭寇到日本的使团,是祖阐一行,还是另有其人?洪武三年、五年和六年的三份咨文和书简,为何会同时保存在北朝睿山?囿于史料的匮乏,这些谜团,目前尚难以解开,只能留到以后继续探索了。
[①] (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Wang Yi-t’ung 王伊同,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368—15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黎光明:《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7本2分,第255—273页;(日)佐久间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洪武帝の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論集》1965年第4期,第15—17页;(日)村井章介:《室町幕府の最初の遣明使について : 『雲門一曲』の紹介をかねて》,(日)今枝爱真编:《禅宗の諸問題》,=雄山阁,1979年,第179—199页;郑樑生:《明史日本传正补》,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7年;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日)Kawazoe Shoji 川添昭二, “Japan and East Asia”, trans. by G. Cameron Hurst III, in Kozo Yamamura,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96—446;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万明:《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7—57页;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赵轶峰:《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古代文明》2013年第7卷第3期,第83—95页;年旭:《<云门一曲>中赵秩遣使内容再探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64—68页;邢永凤:《赵秩与日本——汉诗文中的新世界》,(日)海村惟一、戴建伟、王立群主编:《阳明学与东亚文化:纪念北京大学刘金才教授从教四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5—312页;MA Guang 马光,“Tributary Ceremony and National Security: A Reassessment of Wokou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017, vol. 51, no. 1, pp. 27—54;王来特:《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55—67页;刘晓东:《“倭寇”与明代的东亚秩序》,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②] 仲猷祖阐,生卒不详,道号仲猷,别号归庵、四明桴庵,时为明州天宁寺住持;无逸克勤(1321—1397),字无逸,亦称且庵,绍兴萧山人,时为南京瓦官寺住持。
[③] 有关洪武倭寇活动详情可参考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23页。
[④]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3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843页。
[⑤] (明)吴朴:《龙飞纪略》卷四,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吴天禄等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册,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年,第533页。另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年(以下《明实录》皆同此版),第750—751页;(明)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四,明末刻本,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第21页;(明)陈建:《皇明资治通纪》卷四,明末刻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第20页。陈建的这两种作品中均指十一月遣使安南。除个别字体外,不同书中收录的诏书内容基本相同。
[⑥]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第785页。
[⑦] 《明太祖实录》卷四三,第847页。
[⑧] 《明太祖实录》卷四四,第858页。
[⑨] Kawazoe Shoji 川添昭二, “Japan and East Asi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3, p. 425.
[⑩] 《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七,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349—350页。需要指出的是,洪武元年十一月明朝首次遣使一事在(明)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四,第21页等处有记载,但是首次遣使遇害一事仅见于祖阐、克勤的书信中,其它史料均未见,系孤证。洪武三年三月廿五日明中书省给日本国王的国书中也只是提及洪武二年杨载使团中的五个使者被杀一事,并未提及之前有使者遇害的情况发生。见《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明皇帝书》,《大日本史料·补遗》第六编之三十七,第1—2页。
[11] (明)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并别幅》载:“盖前两年,皇帝凡三命使者,日本关西亲王皆自纳之”,(日)伊藤松辑:《邻交征书》三篇卷之一,王宝平、郭万平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25页。据此似乎可以认为明太祖第一次派遣的使团得到了怀良亲王的接见。有学者持有此观点,见(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下),第183—184页;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第242页;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1卷,第299页。
[12] 明代行人“职专捧节、奉使之事。凡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诸蕃,征聘贤才,与夫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焉”,在内政外交中有着重要作用。(明)张廷玉等:《明史》卷74,中华书局,1974年,第1809页;《明史》卷三二二,第8341—8342页。
[13]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第787页。
[14] Kawazoe Shoji, “Japan and East Asi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3, p. 425.
[15] (日)坂井藤雄:《征西将軍懐良親王の生涯》,苇书房,1981年,第109—123页;王来特:《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60—61页。
[16] 《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明皇帝书》,《大日本史料·补遗》第六编之三十七,第1—2页;(日)汤谷稔编:《日明勘合贸易史料》,国书刊行会,1983年,第28—29页。
[17]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第1056页。
[18] 《明太祖实录》卷五〇,第987页。
[19] 《云门一曲》,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373—374页。
[20] 《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189页。
[21] 《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205页。
[22] 王逢,字原吉,号最闲园丁、最贤园丁,又称梧溪子、席帽山人,江阴人。(明)王逢:《题括苍赵秩可庸两使东夷行卷》,《梧溪集》卷七,顾千里据汲古阁旧藏明景泰刊本校,《知不足斋丛书》第29集,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无页码。
[23] (明)赵秩:《偶作诗并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328—329页
[24] 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第51页。
[25] 明初莱州府设知府一员、同知一员、通判二员。乾隆《莱州府志》卷六《职官》,乾隆五年(1740)刻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第8页;万历《莱州府志》卷二《职官表》,万历三十二年(1604)修,青岛赵永厚堂1939年重刊,第6页。
[26] (日)周佐编:《智觉普明国师语录》卷六,日本宝永二年(1705)木活字版,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第1—68页。
[27] 乾隆《莱州府志》卷六《职官》,第9页;万历《莱州府志》卷二《职官表》,第6页。
[28] 赵孟頫有三个儿子赵亮、赵雍、赵奕,其后代散居在安徽灵璧、山东沂水、湖南湘潭等地。据笔者目前所见三地家谱,暂未发现赵秩的相关记载。笔者猜测,赵秩也可能并非赵孟頫的直系子孙,而是旁系子孙,即其直系祖父可能为赵孟頫的兄弟。赵秩赴日时,为方便交流,故自称为名气更大的赵孟頫后代。此问题待考。
[29] 《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189页。
[30] 赵秩予春屋妙葩诗,洪武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373—374页。
[31] (日)田梅、荒巻大拙:《明使趙秩とその山口十境詩》,《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2010年第14期,第115页;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第61—63页。
[32] 洪武二年赵秩赴日说见于(明)王在晋:《海防纂要》卷七,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一年(1562)自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7册,北京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595页。
[33] 《明太祖实录》卷五〇,第987页。
[34]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六九,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天启四年(1624)徐与参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6册,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年,第518页。
[35] “四年,上遣莱州府同知赵秩泛海,赐玺书,让其王源良怀”,(明)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二,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中华文史丛书》第17册,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1969年,第104页;“四年,上遣赵秩,语其王良怀”,(明)涂山辑:《新刻明政统宗》附卷《日本颠末》,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册,北京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142页;“四年,上以日本未廷,乃遣赵秩宣谕”,(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52页;“四年,遣行人赵秩宣谕。陪臣随秩入贡”,(明)熊明遇:《文直行书•文选》卷十三,北京图书馆藏清顺治十七年(1660)熊人霖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6册,北京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498页;“至四年,遣赵秩语其王良怀”,(明)颜季亨:《国朝武功纪胜通考》卷七,北京图书馆藏明天启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0册,北京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252页;“洪武四年遣莱州府同知赵秩,礼部员外吕渊奉使宣谕日本”,(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四,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商浚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4册,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年,第747页。
[36] 《明太祖实录》卷五〇,第987—988页。
[37]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第1049页;(明)龚敩:《鹅湖集》卷五《赠刘叔勉奉使西洋回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3册《集部》172,第3—4页。
[38]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第1092、1100页。
[39] 年旭将赵秩出使时间认定为洪武三年三月,而爪哇等国当时尚未遣使来贡,故他推测国书中提及的爪哇等国朝贡一事为明太祖故意释放出的一个虚假信息,意在使日本模仿周边国家的做法而尽早向明朝奉表称臣,该观点值得商榷。见年旭:《洪武朝明·日交涉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第14—15页。
[40] 日本山口县立山口博物馆藏,三幅,挂幅装,绢本着色,98.0CM*43.2CM ,http://www.c-able.ne.jp/~daisetsu/tyoutituhitu.html,2014年8月20日。
[41] 山口县立美术馆编:《大内文化の遺宝展 : 室町文化のなかにみる》,山口县立美术馆1989年,第16页。该画作为日本毛利博物馆藏,三幅,挂幅装,绢本着色,100.3CM*33.5CM,http://www.tobunken.go.jp/materials/nenki/13473.html,2014年10月10日。
[42] 赵秩:《关羽画轴》,全球联拍网http://www.uniauktion.com/auction_goods_one_eng.aspx?uid=1081,2016年7月12日。
[43] 匿名:《新訂<櫻云記>》下卷,(日)大町桂月校订:《南朝史传》,至诚堂,1911年,第299页。
[44] 《菊池家代々記錄》,《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573页。
[45] 《明太祖实录》卷五〇,第987—988页。
[46]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第1280—1282页。
[47] 《明太祖实录》卷五〇,第987—988页。
[48] (日)村井章介:《分裂する王権と社会》,第184—187页;Kawazoe Shoji, “Japan and East Asi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3, p. 425.
[49] (明)高岱:《鸿猷录》卷六,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高思诚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册,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年,第16页。
[50] (清)万斯同:《明史》卷一八二《列传》第三三,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续修四库全书》第3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第391页;(清)王鸿绪:《明史藁》卷一二八《列传》第二三,雍正元年(1723)敬慎堂刻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第6页;(清)陈梦雷等编纂:《明伦汇编·官常典》卷四〇九,《古今图书集成》第288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年,第53页。
[51] (明)胡翰:《赠杨载序》,《胡仲子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集部》168,第8—10页。
[52] 《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明皇帝书》,《大日本史料·补遗》第六编之三十七,第1—2页
[53] 以往学者只知祖来来华,其实如瑶藏主当年也一同受命来华,见《菊池家代々記錄》,《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573页。
[54] 《明史》卷三二二,第8342页;《明太祖实录》卷六八,第1282页。
[55] 匿名:《新訂<櫻云記>》下卷,第299页。
[56] (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表章》,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9年,第6页。
[57]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12页。
[58] (明)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宋学士文集》卷二七,上海涵芬楼借侯官李氏藏明正德刊本景印,《四部丛刊初编》第1508册,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29年,第1页。
[59] (明)宗泐:《送祖阐、克勤二师使日本》,《邻交征书》初编卷之二,第82页。
[60] (明)胡翰:《赠杨载序》,《胡仲子集》卷五,第8—10页。
[61] (日)村井章介:《室町幕府の最初の遣明使について : 『雲門一曲』の紹介をかねて》,(日)今枝爱真编:《禅宗の諸問題》,第179—199页;(日)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第240页。陈小法亦认为赵秩并未在洪武四年回国,见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第56页。
[62] 朱本赠梅岩霖诗,洪武六年十月六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203页。
[63] 赵秩诗,洪武六年十月,《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203页。
[64] 赵秩序文,洪武六年十月四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194页。
[65] 赵秩致春屋妙葩书,洪武六年十月初七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197—198页。
[66] 朱本予春屋书,洪武七年三月,《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14页。
[67] 朱本予春屋书,洪武七年三月,《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14页。
[68] 赵秩予春屋书,洪武七年四月十一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68页。
[69] (日)春屋妙葩:《次韵酬本中掌书》,(日)周佐编:《智觉普明国师语录》卷六,第58页。
[70] (日)春屋妙葩:《次告别韵远酬赵别驾二首》其二,(日)周佐编:《智觉普明国师语录》卷六,第64页。
[71] (日)春屋妙葩:《次韵寄可庸别驾,聊伸不忘之思》,(日)周佐编:《智觉普明国师语录》卷六,第64—65页。
[72] 周佑诗,洪武七年三月,《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24页。
[73] 年旭:《<云门一曲>中赵秩遣使内容再探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67页。
[74] (明)朱本:《题长江寺千手堂偈并序》,洪武七年三月望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24页。
[75] 王丹荣、闻鸣:《数词在古代诗歌中的修辞特色及其文化蕴涵》,《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9年第6期,第63—64页;陈文运:《古代诗歌中数字的独特艺术价值》,《文史哲》2000年第3期,第61—64页;史玮璇、王丽静、张立艳:《解读古典诗词中数词的模糊性》,《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年第6期,第191—192页。
[76] (明)克勤:《寄题吞碧楼》,《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68页;《邻交征书》二篇卷之二,第194—195页。
[77] 无逸克勤诗,洪武七年三月廿二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17页。
[78] 年旭:《<云门一曲>中赵秩遣使内容再探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64—68页。
[79] 《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明皇帝书》,《大日本史料·补遗》第六编之三十七,第1—2页。
[80] 赵秩致春屋妙葩书,洪武六年十月初七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197—198页。
[81] 此处原文有小注为“勒、阐等十僧”。“勒”当为“勤”即无逸克勤之误。
[82] (明)王逢:《题括苍赵秩可庸两使东夷行卷》,《梧溪集》卷七,无页码。
[83] 赵秩序文,洪武七年三月,《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22页。
[84] “秋”当为“秩”之误。
[85] 朱本,字本中,号四明山櫵,时为御史台掌书,与赵秩同往日本。“大明国使御史掌书四明朱本”,见于《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191页;“大明国使太微执法侍史四明山樵朱本本中”,见于《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37页。
[86] 《宝幢开山智觉普明国师行业实录》,(日)周佐编:《智觉普明国师语录》卷八,第12页。
[87] (明)王士骐:《皇明御倭录》卷一,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3册,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第7页。
[88]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第1282页。
[89] (明)薛俊:《日本国考略·补遗》,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金骥刻本,姜亚沙、陈湛绮主编:《日本史料汇编》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影印本,第84—85页。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明)陈全之:《辍耰述》卷四,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一年(1532)书林熊少泉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296页;(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六九,第519页。
[90]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二,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宪刻本,《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明)王在晋:《海防纂要》卷七,第595—596页。
[91] “三日”或为“五日”之误。“祖阐受命而行,自翁洲启棹,五日至其国境”,见(明)宋濂:《恭跋御制诗后》,《宋学士文集》卷二八,《四部丛刊初编》第1508册,第13页;“无逸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昼夜即达昌国州,已而赴南京,仍见上端门”,见(明)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宋学士文集》卷二七,第1页。
[92] (明)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并别幅》,《邻交征书》三篇卷之一,第226页。类似的内容同样见于(日)瑞渓周凤:《善邻国宝记》卷上,(日)田中健夫编注,应安六年癸丑,大明洪武六年,集英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
[93] (明)宋濂:《大明故中顺大夫礼部侍郎即曾公神道碑铭》,《宋学士文集》卷十七,《四部丛刊初编》第1506册,第4页。
[94] 《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183—184,197—199页。
[95] (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下),第186页。
[96] Wang Yi-t’ung,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368—15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4.
[97] (日)佐久间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洪武帝の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論集》1965年第4期,第15—17页。
[98] 郑樑生:《明史日本传正补》,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99] (日)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校仓书房1988年版,第251页。
[100] 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第116—117页。
[101] 赵秩致春屋妙葩书,洪武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371—372页;赵秩致春屋妙葩书,洪武七年四月十一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67—368页。
[102] (明)克勤:《送周允上人归丹后偈序》,洪武七年三月廿二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20—321页。
[103] 赵秩致春屋妙葩书,洪武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371—373页。
[104] 赵秩序文,洪武七年三月,《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322—324页。关于洪武七年入明僧详情,可参考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第135—151页。
[105] 《明太祖实录》卷八九,第1578—1579页。
[106] 年旭:《<云门一曲>中赵秩遣使内容再探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68页。
[107] 赵秩致春屋妙葩书,洪武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371页。
后记
拙文为《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文史哲》,2019)的姊妹篇,曾在2014年10月“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公开发布。《面子与里子》一文太长,评审专家建议将繁琐的考证删除,以免枝蔓太多,影响主体观点。于是,本人将赵秩使日这部分,剔除出来,单独成文,遂得此篇。小文解决了一些小问题,但更多的谜团,囿于史料,依然扑朔迷离,期待后来者继续深究。
文章虽早于2014年就完成初稿,但因一些重要的史料,一直未能找到,且未做实地调查,故一直未刊发。2019年夏,又专程去浙江湖州等地考察赵孟頫家族的故乡,获得了多位乡贤的大力帮助,也得到赵氏后人的支持,提供了一些家谱等重要资料,在此谨致谢意。
小文虽短,但注释繁多,多亏潘清老师反反复复的耐心打磨,才得以面世,再次感谢潘老师的辛苦编辑。
以上文字为初稿,未经编辑。正式引用,请参考PDF。
部分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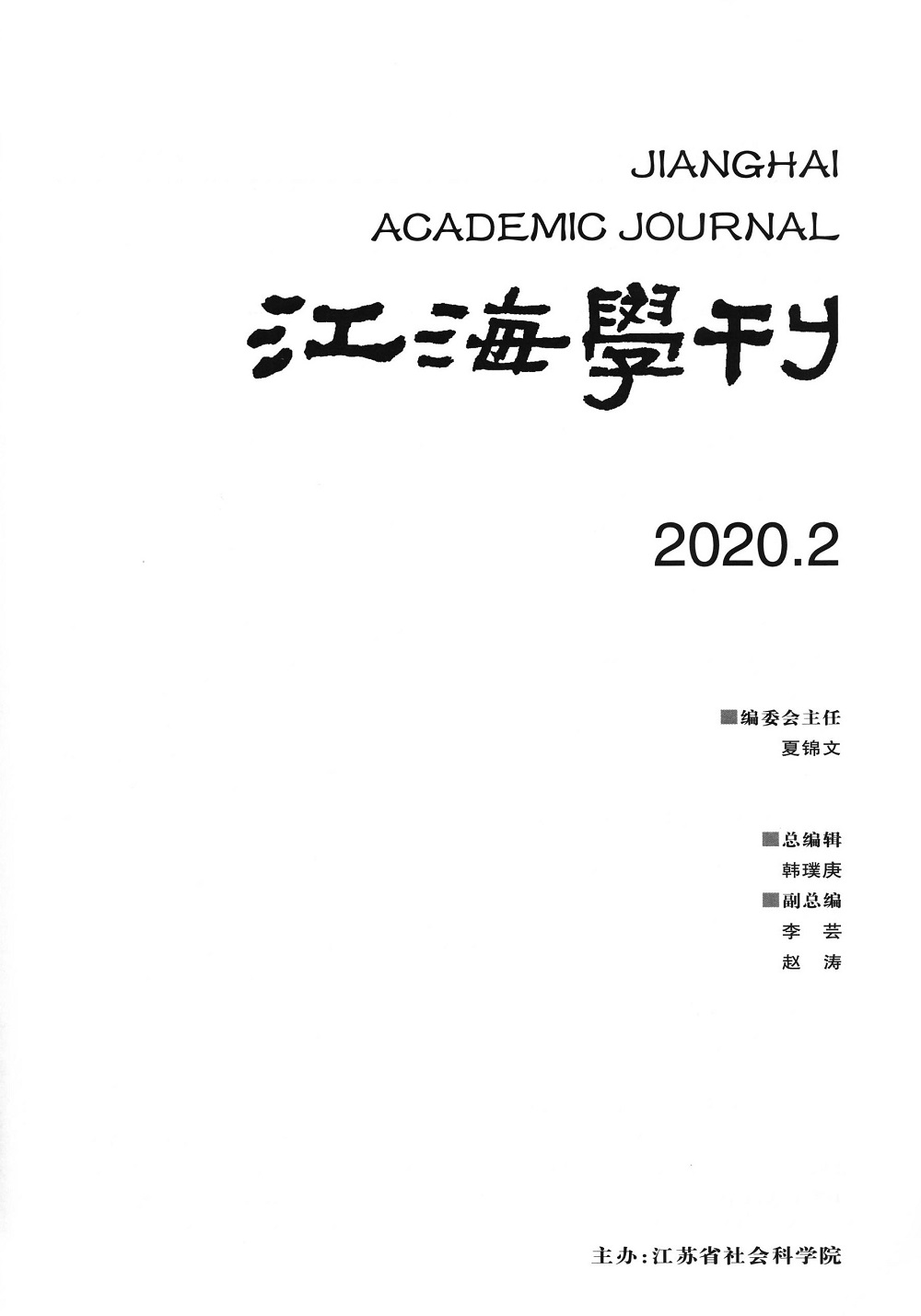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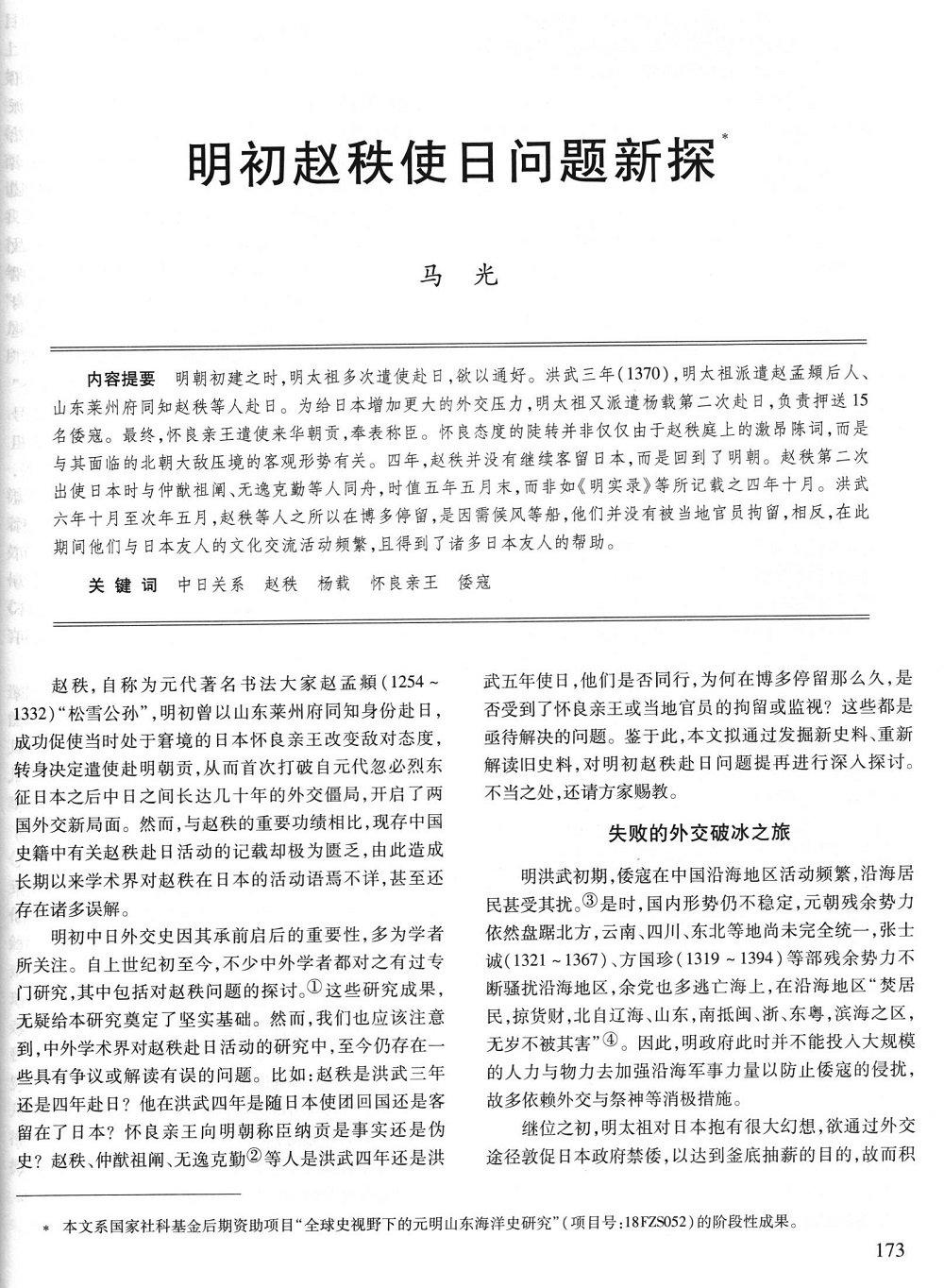





马老师这个充分发掘中日双方史料的意识真的是令人佩服,文中多处对大日本史料的活用确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2010年的日韩历史共同研讨会上,日本的中田稔先生就提到了对于倭寇问题的研究应该在充分结合中日韩三方史料的基础上力求突破。想必这种研究方法与意识也将成为今后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
小文尚有不足之处,还请多指正!